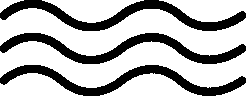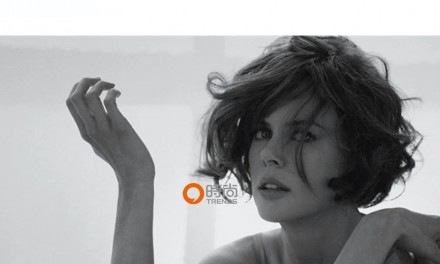对许多人来说,乘胜追击是理所当然的事,可胡歌偏偏是逆流而上的性格。许多问题他都曾苦苦想追求一个答案,现在却能接受无常才是常态的事实。他想明白了,松弛了,新的角色和新的篇章也一起开始了。
那天最后的记忆是被拽上台,被大家抛向空中,两下过后,胡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酒到底还是上了头。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杀青宴上,好多人都哭了,可他没掉眼泪,只是碰了一杯又一杯。4 月 1 日进组, 10 月 1 日杀青,整整半年,竟然就这样过去了,感慨有,高兴有,他心里各种情绪交杂出的复杂层次,眼泪可能不足以概括。
差不多又是半年后,某天夜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,是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消息。那些日子他略有失眠的困扰,这下干脆兴奋到天明。之前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去戛纳,他都婉言谢绝,他希望以演员的身份、带着一部作品踏上心里的“电影至高殿堂”。
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去戛纳,是荣誉,也算是实现了他一个“小小的目标”。出发前,他没忍住先看了次电影成片,“满意谈不上,但我觉得值得,不虚此行,至少我找到方法了。”他说的是表演,于生活本身,创作这个角色的旅程也平息了那些曾经翻江倒海的忐忑,被他认为“过誉的评价”所带来的惶恐,对于自身不断反省所带来的不安,都渐渐尘归尘,土归土。
如果一部戏得到了认可,那就再演一部更好的——在胡歌的想象里,这本应是一个演员自我追求的道路。可蜂拥而至的关注让他不得不分心去应对许多力不从心的事情,他感到疲倦,又不知如何斩钉截铁地拒绝。对许多人来说,乘胜追击是理所当然的事,“可我就是非要逆流而上的性格。”
几年前曾经有篇采访,说的是他骑摩托车长途旅行的故事,用了类似“胡歌和自己的一次妥协”这样的标题,朋友转给他看,哈哈大笑说“矫情”,他却不自禁地想了很久。“反过来想,是不是平时我一直都不愿意和自己妥协?所以那一次的旅程是所谓的任性、难得的妥协。”
什么才算“妥协”呢?或许只是随心所欲做些不管不顾的事情,安心享受触手能及的快乐。可那只是一时一刻,无论曾经取得了怎样的成绩,他似乎总是归结为“天时地利”,然后用更苛刻的眼光打量自己,主动站到和自我对决的位置上,心里还会冒出一个声音,“还有别的可能吗?”
第一次见刁亦男前,胡歌没有做任何准备,他不想“临时抱佛脚”,刻意把自己变成导演心目中的样子,“我只想让他看到我当时最真实的状态。”两人约了顿平常的饭,他对刁亦男的第一印象是“非常儒雅、非常低调内敛”,也庆幸有个中间人在,“不然可能我们许久都憋不出一句话来。”他心里高兴,“看来气场挺合的。”
拍完电视剧《猎场》后,胡歌几乎有两年时间没有接戏,剧本纷至沓来,却没有让他有创作冲动的作品。许多人无法理解他的隐身,也无法理解他对“驾轻就熟”这几个字的警醒,当“梅长苏”这个角色把他再次推到公众关注的顶点后,他知道是时候再次切换轨道了,可这一步怎么迈,他没有答案。三年前我见到胡歌时,他带着点怅然,用“不学无术”形容自己,又用极严厉的词语评价那些叫好叫座的角色——那时他渴望停一停,体会充实而饱满的生活,希望真正的自己可以追上旁人眼中的自己。
“所以有人说刁亦男导演想约我见一见的时候,我想,这可能会给我打开另一扇门。”看完剧本后他只有一个念头,我能演周泽农吗?一个始终在暗不见光的夜色中逃亡的犯人,他完全没有演过这样类型的角色,电影构建的那个世界与他的现实生活和经历也相去甚远。与文艺片导演合作,而且还是上一部电影拿下过柏林电影节大奖的导演,自己行不行?他暗自揣测,导演或许和自己一样忐忑,“一直在偶像剧和商业电视剧作品里摸爬滚打那么多年的演员,他没有用过。”
刁亦男之前看过他不少剧照和广告作品,“比较青春小生的感觉”,但一张杂志封面照片让他觉得,胡歌有他所期待的硬朗潜质。在见到本人前,他心里已经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确定,“我相信可以和他合作顺畅,如果演员和大家对角色的想象有很大的距离,反而更能激发我的一些创作激情。”剧本他已经磨了两年,又因为档期等问题等了一年,他对胡歌志在必得。
第一次见面时,胡歌就直言了他的困惑,接到剧本后,他再次向导演坦诚了自己的顾虑和压力,刁亦男安慰他,我们有很多时间准备,可以慢慢来。他们约着长聊过一夜,一人一瓶红酒,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和感受,有了这样信任的基础,胡歌更放心把自己完全打开,“不管成败与否、结果如何,我想去冒一次险。”
刁亦男给他加了颗定心丸,“导演说,我是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,不会对不起我的作品。”他让胡歌做好心理准备,“现场达不到要求就不会喊‘过’,可能会拍很多条。”“拍很多条”的情况的确出现过几次,但完全没有影响胡歌的信心,“重复再来的时候,如果你无法调动或者无法复制情感,只能说你不够职业。如何合理巧妙运用真实的情感是衡量一个演员专业性的标志之一,它考验的是演员的准备度和切入点。”
他也理解,导演用重复的方式来寻找更多可能性的同时,偶尔也在故意借机打磨演员的自信。“表演时如果过于自信,演员往往会陷入一种所谓的模式里去,他会觉得我这么演是最准确、最有感染力的,反而会把其他的许多敏感性关掉。”他警觉这种偏执的滋长,“演戏的时候,你内心是否有这个支点,自己是一清二楚的。如果完全是靠经验或是一些技巧,或者记所谓的节奏动作,那你就只有技巧,没有情感,整个是跳出人物的。”他觉得不能对任何一种表演方式妄下是对是错的断论,殊途同归,结果是要观众“相信”。
与刁亦男合作过《白日焰火》的廖凡也参演了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,他有些惊讶,这部作品会呈现出与以往如此不同的风格:之前的故事更为完整,情节的解扣、人物的描摹更容易让观众过瘾,可这一次,刁亦男用更意向化的方式强调视觉冲击感,人物的内心往往直接用环境的描绘传达。在廖凡看来,这要求演员去寻找“如何在其中铺开”的方式,空间更大,表演也更求精准。
对过往作品大部分是电视剧的胡歌而言,他必须用十二分的敏锐来迅速摸索更合适的表演方式。电视剧胜在容量,可以把人物建立起来后慢慢铺垫,“哪怕有几场戏不对,你也有足够的空间来补救。但电影不行,每一帧你都必须在人物里,哪怕一个镜头跳出来,也会非常明显。”这次的台词也被摆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上,有时拍上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几句,他意识到,电视剧惯有的宏大台词量让他的准备习惯有所偏颇,“以前拿到剧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台词拿下来。但往往我把台词看得太重要了,以至于很多时候在演台词,而不是演人物。”
他试着尽可能在表演中减少技巧的成分,“我不能完全做到不露痕迹,但只要出现一点那种感觉,导演马上就能看出来。”眨眼是一次还是两次有分别,呼吸起伏是强是弱也有分别,这种“用放大镜式的”苛求方法让他时刻紧绷着神经,“非常好,以前很难有那么高的要求,逼着我往人物的内心去走。”
第一次围读剧本用了近三小时,胡歌看到刁亦男默默流下的眼泪,心里暗自惭愧,“我为什么没有被这样感动?”后来他总是说刁亦男的“任性”,“导演一旦进入创作的状态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,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,他为了达到心中想要呈现的效果,是不计成本、不问代价的。”
这也让他更渴望掏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。进组第一个月还是准备期,尚未开机,心理压力加上对环境的陌生,胡歌已经在一种无所适从中徘徊。其间他得了一次肠胃炎,加上发烧,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平息下去,“吃了药也没用,可能是精神性的。”之间导演问他,最近感觉如何?他回答,好,也不好。
“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身体上的不适,我都留着,因为它们让我更接近角色。一个逃犯,戏里几乎 90 %的状态都是不安和焦躁,我没有必要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自信满满和舒服的状态,不舒服才是对的。”
胡歌评判一个角色的难度标准,在于自己是否能快速进入那个角色,并抓住他的内核,“周泽农,难。”精神和体力上的消耗也带来双重压力,杀青比原定时间延迟了一个多月,闷热的武汉夏夜一个个熬过去,最后他竟盼着早些结束。电影《李娜》中的“姜山”一角相对没有如此大的压力,可在接到导演陈可辛的邀约时,他一样不自信而且满腹担心。
“接到邀约时,我完全没准备。”但剧本出自编剧张冀之手,他喜欢,加上陈可辛那句“我需要一个观众心目中的姜山”,他被说服了。他本来就对网球有兴趣,一直敬佩李娜,但心里有道坎不知该如何迈过,“如果《李娜》中演的是生活中的李娜,那如何能让观众相信姜山就是我?”
胡歌对陈可辛提了一个要求,要我演,我就必须见一次真人。他已经看过许多有关姜山的采访和视频,“从外形上去塑造他,可能比较难,但见了姜山本人之后,抛开视觉上的因素,我觉得他身上很多可爱、温暖的地方都是可以去表现的。”电影的时间跨度不小,姜山的体形由精壮到发福再瘦回来,胡歌自觉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如此剧烈的转变。“我想好吧,我把人物的外在部分虚化,着重去表现这个李娜背后的男人的内心。”
他这一两年里合作的这些导演,对电影的要求普遍是“克制”,和电视剧里那种释放感不是同一个频道。自己的角色在整部作品中应当承担的任务,他有了更精准的判断,追求自我的标准之外,他更多从作品的需要去权衡角色的分寸。这些角色都让他尝试了不同的表演感受,可以更沉重一些,也可以更轻松一些。他曾苦苦思索,如何用生活赋予角色更鲜活的底色,如何更准确地拿捏真实与戏剧之间的比例,可当他用更简单的方式去拥抱一个角色的时候,反而从中得到了生活的启示。
《如梦之梦》他已经演了六年,每一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、和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去做同一件事,这种形式感让他有了种错觉:好似之间那一年的一切,不过是大梦一场。“大概是从第三第四年开始的。比如说去年的今天,我在北京保利剧场晚上几点钟说了这句台词,隔了一年,我又在同一天、同一时间、同一个地方说这同一句台词……你会发现,相隔一年的这两个时刻是可以重叠的。”
每一年,这种感觉都会更加深刻。“就好像我昨天晚上在床上躺下睡着,做了一个很长的梦,梦里我去了很多地方,做了很多事情,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在床上,还是盖着同一条被子,还是原来的姿势……在舞台上的这一刻反而是真实的。”
在某一轮演到第五第六场的时候,开场前的那一分钟他还在念着“还要再来一遍”,但临上场了,迈出第一步前他深吸了一口气,“来吧,梦又开始了,让我看看今天会有什么不一样?”这是演戏最真切的感受,也让他对人生有了另一种解读的视角,“我们以前接受的概念,都是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,只要我们相信,只要我们努力,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会有希望。可有时偏偏不是这样的,我们要去接受残酷和无常的一面。”
并非是某个突然瞬间的顿悟,但他渐渐明白,他的执着促成了自己一次次的蜕变,也差一点让自己陷于牛角尖里彷徨,但幸好,他没有“把牛角尖钻破”,而是适时返身而归。“现在我学会跳出来看自己了——当看到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时,我看到自己也在不停变化。之前纠结的时候,我找不到答案,而且接受不了,觉得一定需要一个答案。但现在我知道,无常才是真正的常态。”
不久前,胡歌有几位藏民朋友到上海来看他,他们看到上海高楼大厦和夜晚不灭的霓虹时的兴奋,让胡歌想起了自己在高原时的心情。高原并非世外桃源,城市也非牢笼,它们对不同人而言,都是“在别处”。
“你所有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环境似乎有直接的关系的。我们从小成长在城市里,其实也被局限在城市的视角里,突然改变了外部环境,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时,会觉得心里特别平静,看到人类的渺小。可并不是那里的环境真的比城市更具哲学意味,只是我们跳出原先世界的时候,心被打开了。”
每个人都要找到内心的幸福感,找到一个支点,“别处”会带来一时的开阔,也会让获得幸福的途径更多元化。这几年胡歌去了好多次青海和长江源做公益活动,在那些地方他常常会问自己,在这里,我究竟可以干什么?
“比如去‘绿色江河’,我刚开始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那里对志愿者的专业要求还挺高的,身为一个演员,我好像力不从心。”但创始人告诉他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,即使是一个组织能力也有限,但公益最重要的是用实际行动去转变其他人的意识和观念,“我的作用就是传播和宣传。可能我改变不了现状,但从我做起,至少有人会看到我们在做些什么。”
但“别处”终究是暂时的,想象永远和现实间存在些落差,“更好些或是更坏些都有可能。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,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,我都不会后悔,哪怕过程很揪心。何况对演员来说,说不定某天这种体验就能被用到。”
被理解还是被误解,他已经不那么在乎了。表演是一种单向输出的方式,他并不需要即时的肯定来做判断,也不会因此感到孤独,“而且我不怕孤独,我一直都需要和自己相处的时间。”他也更能坦然地面对无常,“接受了无常后,你才更容易获得幸福感。你不能总是想维持某种状态,不能总是害怕失去,因为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。”